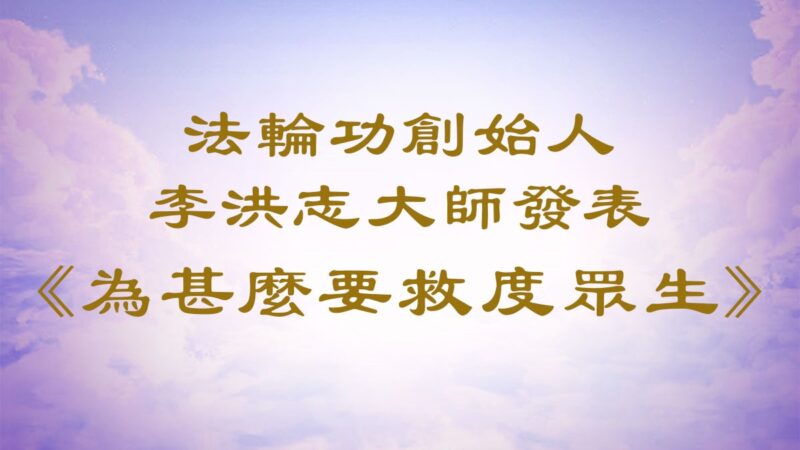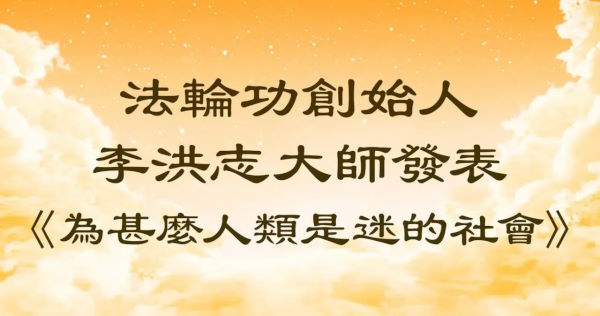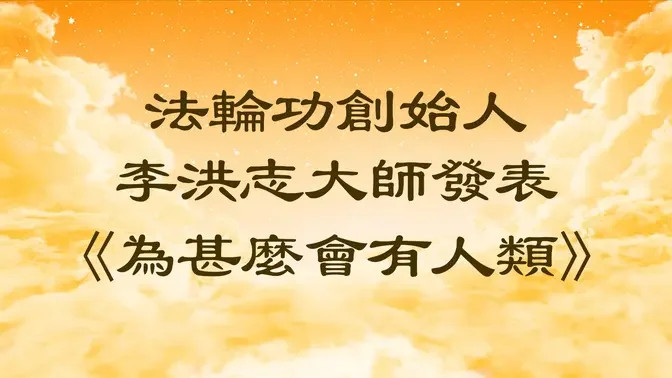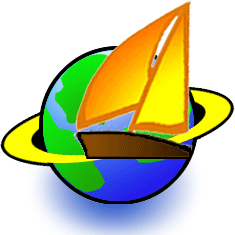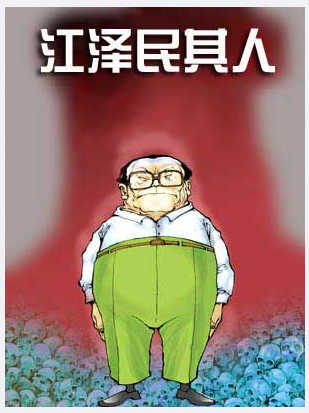八十年代中,同几个朋友谈论《古拉格群岛》,有人建议,应当搞一种“公墓文学”,选一些文革中的受难者作代表,将他们的遭遇如实记录下来,分门别类,编成丛书,如教师公墓,作家公墓,演员公墓等。这个建议得到大家赞同,并在纸上拟了一个初步的名单,甚至连书的封面也想好了,上面是一个纪念碑,簇拥着白花,以示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后来这心愿没能实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最初看到王友琴女士的《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一部关于普通人的受难实录——我心里顿时充满感佩。1980 年,她还在北大时,基于当时发表的文革行状与事实相差甚远,就已开始搜集撰写文革死难者的事迹。做这件事,对她个人没有什么好处,不能靠此升职称和分房子,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这些她都不在意,她把自己称作“历史的义工”,默默地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此后在美国见到面,更是感觉她的人,一如她文字的朴素。房间里没有什么家什,书架上却堆满了采访记录的卷宗。据她说,有一千多人。足以建成一个小小的文革资料库了。
采集这些事例,想必花费了她不少时间和精力,而且不是每次都成功,有些人是由于回避,不想让心灵再受一遍煎熬;有些人是出于害怕,因为那些迫害者尚在,并没受到任何惩罚;而有些人则是因为反感,甚至质问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查。
是呀,为什么呢?要知道,文革已过去近三十年,早已盖棺论定,何必再让往事缠绕心头,就像文革后的一首歌所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对此她在前言里如是说:“在对人的残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和斯大林
迫害古拉格群岛上的囚犯,性质、规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这一方面的真相,被写出来的还非常稀少。由于不被记录和报告,文革的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文革曾发生过大规模的迫害,残害了许许多多的生命。尽管八十年代出过一些纪实文学,那也只是轻描淡写地纪录了很少一些受害者的遭遇。由于实录普通人的受难,展示公开的虐杀,会让人们对文革的官方结论产生怀疑,其结果就是,在二十世纪历史上,还没有一桩暴行像文革这样,大量的事实没有被记录下来,没有被公布出来,没有被讨论起来。
在前言里,作者还讲述了一则见闻,一名曾蹲过劳改农场的教师告诉她:在杀过牛的地方,牛群每当被驱赶到那里,便会哞哞悲叫,而在杀过鸡的地方,鸡群会照样嬉戏欢乐。对待死去的同类,作者正是选择了牛的方式。还有那些接受她采访的人,于牛与鸡之间,记忆与遗忘之间,他(她)们也同样选择了前者。在作者心中,这些普通人 “在人性中挣扎奋斗而趋向善意的力量”,曾不止一次提升了她的勇气和信心。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历史使命感。为此,她感谢每一位受访者,感谢之前她们素不相识,如今通过访谈、电话和写信,却在一起追寻往事,分担人生经验。
法国作家加缪曾经这样说过:“作家的作用与艰巨的义务紧密相连,正因为他是作家,在当今这个时代,他就不可能为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服务,他要服务的是那些承受历史的人。”加缪的时代,世界正处于分裂状态,所以他呼吁作家要有独立性,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写作。在当今中国,像加缪所说的那种作家和学者,可谓寥寥。许多
知识人的文字,其实都是在为权力服务,或者为金钱服务。而王友琴的全部写作,却是为了那些“承受历史”的普通人,为了写出一部受难者的历史。
多年来,我们已习惯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说法。然而,在漫漫的苦难中,人民又何曾创造过历史?他们所能做的,常常是被迫承受英雄(权力者)创造的历史。文革的暴行,曾遍及全国各个阶层,深入每一个家庭。受到迫害、监禁和杀戮的,上至国家主席、各级官员,下至教师、医生、工人、农民、保姆和家庭妇女。但文革之后,权力当局却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中,按照不同的待遇,披露一些文革中受难的高级干部和社会名流的生平(对于文革的发生,其实他们也有一份责任),不是为了真相,而是为了恢复名誉。而那些“承受历史”的普通受难者则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讲述他们,这就使得文革的全部镜象被歪曲,被遮蔽。即使是那些普通受害者,也将自己的遭遇视为当然。作者采访过一位中学老师,他在文革中曾和被打死的人关在一起,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些写出来,他说既然国家主席都受到那样的迫害,自己一个普通教师受的苦又算得了什么。也许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话感到悲哀,在这位中学教师的潜意识里,像他那样的文革中的普通人,不过是“承受历史”的人而已。既不可能创造历史,也不奢望进入历史。他这样说,想必是出于无奈,“他只有把自己视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对他身遭的不幸而产生的愤怒与压抑稍有缓解。”从而寻求心理上的平衡。正是由于此,作者立志为这些普通受难者而写作,讲出他们想说而没能说出的话,以记忆对抗遗忘,就更显出她的良知和勇气。
上面加缪那段话的深意还在于,只有关注和描写那些“承受历史”的人,而不是“创造历史”的人,我们才有可能了解真相,认清事物的本质。《纪念园》分四个部分,有“受难者名录”、“死难发生地”、“纪念文字”和“研究与评论”,主页上写着“我们没有忘记你”,死者照片都饰以白色的菊花。其中搜集了他人写的文章,如著名的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的屠杀事件,但主要还是王友琴自己采写的实录。这些实录并不是单纯的资料,作者采用《史记》的互见手法,以专门人物立篇,又常在他篇中提及此人物,穿插交待背景,成为有系统的历史著述。索尔仁尼琴曾把自己的《古拉格群岛》称作“文艺性调查初探”,除了调查不能周全,许多事未曾亲历,试图用一种整体的观点,将各种事件联结起来,也是原因之一。任何历史叙述都是拥有自身话语的叙事,王友琴女士的采访实录当然也不例外,她常
将自己的思考贯穿其中,夹叙夹议,加以分析,堪称“发愤”之作,而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品质,还是一种求真的精神,用索尔仁尼琴谈自己著述时说的话来评价,那就是其中“所写的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
由于采访条件的限制,作者所记录的专篇人物大多是北京人。在这些人中,有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教师孙历生,北京二十五中教师陈沅芷,北京八中教师华锦,北京六中老校工徐霈田,北京东厂胡同居民左奶奶和马大娘,中科院考古学家陈梦家,气体厂工人陈彦荣,民国名人张东荪一家三口,北大教授董铁宝,北农大职员何洁夫,北大教授吴兴华,北京玻陶设计院黄瑞五一家五口,陆军总医院医生刘浩,北京台型机床厂会计孙启坤,北京六中学生王光华……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名单,他们中有的是被打后自杀(很多自杀其实是虐杀),但多数是被直接打死的。当然,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到底有多少。有人曾写文章推算,受迫害的达一亿人,被迫害死的至少二百万人以上。而文革后各地编写的大事记里,写出死者名字和死亡经过的,相当罕见。
对于文革中的死亡,有一个标准用词——“被迫害致死”。这一说法被用在各种回忆录里,它掩盖了自杀与他杀的区别,更掩盖了打死人的过程,从而使这段历史不致显得那么残酷。作者在实录中详细描述了这些人物的死,有的以前也曾披露过,但作者描写的细节,在几十年后还是骇人听闻。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她是在学校操场上,被带钉的棍棒长时间当场打死,另一个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终身需要穿着钢背心。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绑在葡萄架上,施以带铜扣的军用皮带,然后又用沸水从头顶浇下去,回忆者说凄惨的叫声响了半夜,那声音“像杀猪一样”。孙启坤在家里被鞭子蘸着水打,皮肤被打得全变了颜色,还被用绳子一松一紧地勒脖子。李丛贞被棍棒皮带打死后,还被人用刀在他身上劈下一块肉,看是不是装死。吴兴华在酷暑烈日下,被逼喝下化工厂排出的污水,死于急性痢疾后,家人还得被迫同意解剖尸体,以证明他是拿自杀对抗运动。黄瑞五一家五口则是被捆绑着跪在地上,用一阵乱棒打死。这样的残杀也是有名目的,纳粹称之为“最后解决”,前苏联称之为“最高方法”,文革虽然没有从上面直接下达过打杀人的指令,但也可以称之为遇罗克所说的“连根拔”。我不知道作者在写下这些暴力情
节时,是如何忍受过来的。据她说,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她就常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倍感压抑和低沉。
文革曾被狂热参与者称作“红色恐怖”,各个阶段都曾发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但作者指出, 1966年早期红卫兵发动的“红八月”,1968年革命委员会治下的“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死亡最多的两个时期。“在这个网站上被记录的文革受难者,绝大部分的人都死于这两个文革的死亡高峰期间。”有一种说法,称文革是无政府主义,后来的当政者的诫惕心理无不渊源于此。但事实表明,文革的迫害完全是有组织的,受到控制的。以上这两个时期都是政权机关相对稳定的时期,发生的暴行都是在政权名义下针对无权的群众。每次大规模残害发生前后,报纸上都有公开的社论表示支持。施害者受到明显的权力指使,受害者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尤其在“红八月”中,红卫兵在北京城四处抄家打人,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在1966年夏天,仅北京市就有1772人被打死(见《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又有许多人被打死或自杀。“革命委员会”后来被彻底否定,其中的造反派成为“三种人(他们当然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早期的红卫兵运动,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最初的红卫兵运动产生于 1966年6月,由中学里的高干子弟发起。其活动从六月到十二月,横跨工作组和中央文革两个时期。工作组是由当时主持文革的刘、邓派出的,他们沿袭反右与四清的作法,把大批老师、学生打成反革命右派,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资反路线“五十天”。红卫兵创立伊始,认为这次运动仍然会像过去一样,目的是整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于是在工作组的指使下,带头起来造学校干部和老师的反,并在七月份工作组撤出后,制造了“红八月”的暴行。1966年10月以后,由于父母受到冲击,这些红卫兵开始反对中央文革,遭到打压,遂告瓦解。他们的遭际
反映了党的领导层对待文革的分歧,而对于许许多多普通人来说,无论是工作组时期还是中央文革时期,其悲惨命运都是一样的。
卞仲耘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六月一日,北师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三个学生贴出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此后工作组进入学校,支持高干子女掌权,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都是四清对象”,在教师学生中划分左中右,把许多人打成反革命。卞仲耘被定为“四类人员”,罪名之一就是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因分数不够没被附中录取。在工作组对她召开的批斗大会上有的学生用民兵训练的步枪捅她脊背,倒地后又被揪著头发拖起来,工作组未加干涉。七月底,因毛泽东不满工作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其实那时打人已相当严重),工作组撤离学校,红卫兵独掌大权。八月五日,卞仲耘就在红卫兵的批斗大会上被活活打死,死在她的学生的棍棒之下。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对宋彬彬说:“要武嘛。”宋因此而将名字改成“宋要武”。自此,文革第一波暴行迅速蔓延到整个北京及全国。
文革甫起,老红卫兵一度成为革命的主宰,大肆宣扬“血统论”,所以打老师同学也特别狠。这些红卫兵即使不去打人,也会成为当然的接班人,正如文革初清华附中的一张大字报所说:“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谁也没有反对他们接班!),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极度扩张的特权感,把打“阶级敌人”视为荣耀和考验,并且深知不会受到任何法律惩处(事实上也是如此)。作者曾引用一个前上海中学红卫兵的回忆:“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著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在这样的“革命气氛”中,那些被红卫兵视作“黑五类”的人,当然是在劫难逃了。从实录揭示的事实看,他们的罪名大多是因为家庭或本人身份,如实录中提到的卞仲耘是基层教育干部,文革初就被工作组定为“四类”,王光华和左奶奶的家庭成分是小业主,陈彦荣母亲土改时被划为富农,黄瑞五和孙启坤则是家有房产,陈梦家是右派,至于马大娘和李丛贞,一个是帮工,一个是工人,应当属于革命政权的基本群众。这些人在平时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从不对现实不满,也没招谁惹谁,即出
于发动文革的最高和最低目的,也找不到非杀害她们不可的理由。但他们还是被权力杀害了,倒在历史的轮下,变成一道巨大的阴影。对无权者的残酷,是文革的一大特色。二十世纪希特勒的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或可与之相比。受到历史决定论的召唤,纳粹以种族斗争的名义,要消灭犹太人,而斯大林和文革则是以阶级斗争的名义,要消灭其它阶级。他们都号称要拯救世界,却蔑视“你不可以杀人”的人类古老律条,以人的血统分类,用鲜血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直至疯狂杀戮,血流成河。在《艾奇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谈到纳粹杀害犹太人的行径,汉娜‧阿伦特写道,这是“任何实用目的都无法予以解释的一种罪行。” 这里除了一部分“人类”的权力傲慢和优越感,还什么呢?说到底,文革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不是党和人民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也不是官僚主义与反官僚主义的矛盾,而是权力者对无权者的暴政。这样的暴政常常并不出于任何实用目的,迫害的唯一理由,只是缘于受害者的身份。诚如汉娜‧阿伦特所说,它 “攻击人的差异,也就是说,攻击‘人的身份’特性,没有这种特性,‘人种’或‘人类’一类词便会毫无意义”。
自文革结束,许多受难者的家属一直要求讨回公道,试图在法律上追究具体责任者。卞仲耘的丈夫多年来就是这样,他的努力没有成功,检察院先是以“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后又以属于“运动中的过激行为”,而决定不予起诉。文革持续了十一年,然后又过了两年才被彻底否定,文革初期的罪行自然已过了时效,但想来问题还是在“运动”一词,因为它涉及到最高权力者,也涉及到个人在政权名义下的行为责任。后者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可以暂且不谈。管如此,当年的打人者至少应当在道义上,向受难者及其家庭道歉,求得宽恕。我们至少应当响应巴金的呼吁,将大量的文革暴行记录下来,公布出来,讨论起来。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让集体失语主宰我们,何来正义的伸张?又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
就像布罗茨基说的,“时间只能使邪恶升值”。经由犹太幸存者和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不懈努力,纳粹大屠杀和前苏联大清洗早已大白于天下,世上再也无人敢于公然为之辩护。但文革暴行却未曾受到如此充分揭露,这段历史成为空白,不到三十年时间,文革后的一代人对此已茫然无知。一些文革领导人和积极参与者也开始发表文章,为自己百般辩护,以至在某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眼里,溃疡也变成了花蕾。我就见过国内一份有名的读书杂志,遮遮掩掩地讴歌文革中的农村民主,好像农村从来没有过批斗 “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大兴县和道县的屠杀更是天方夜谭。而受难者历史的缺失,也使得一些空谈理论的西方左派能够从全球文化革命的观点,去论证文革的历史合理性。曾看到一篇文章讲,作家郑义撰文谈文革中广西的吃人事件,经瑞典一些报纸摘译发表后,几位社会学家竟批评说太荒唐,认为这是出于对东方民族的偏见。 看来有一天,他们甚至还会告诉我们,所谓文革暴行,不过是后殖民主义话语,是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
所有这一切,都更显出王友琴写作的意义。
2003 年在美国芝加哥见到王友琴时,她正在联系出版书的事,说是北京有出版社愿意考虑。最近她来信说:“我的书在香港出版,已经发了广告,5月初印好。书名是《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50万字,有麦克法夸尔和余英时先生的序言。”末了,她又不无遗憾地加上一句:“在北京最后未能出版。那是一个35万字的版本。他们排了纸样,可是北京的出版社不接受。”
没有受到历史追究的罪行是不会被宽恕的,更不会被遗忘。
那就让我们等待吧。
—-转载<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