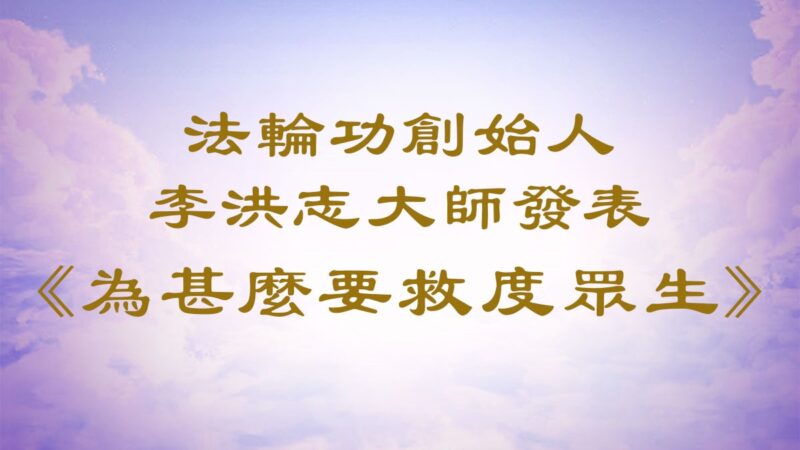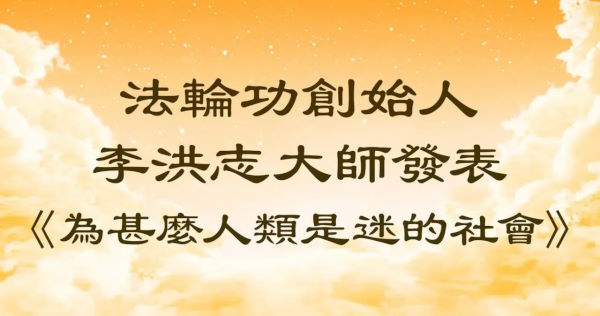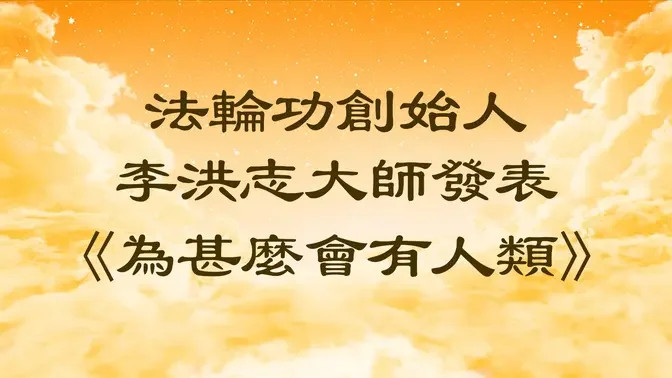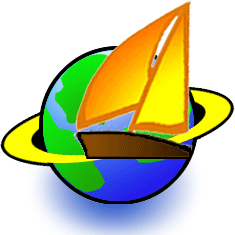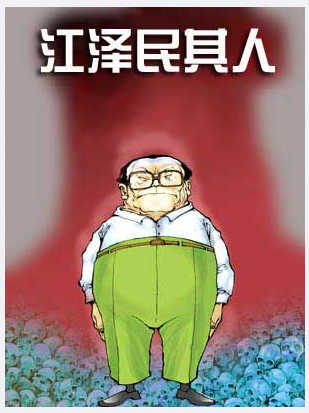我是1944年出生的,1949年共产党来的时候,我才5岁。我父亲是国民党的中将,陆军野战兵的一个军长。1948年底他正在淮海打仗,随着国民党战败,去了台湾,我妈带着我和弟弟留在了大陆。在中共眼里,你家人去了对面,还活着,还在跟这边作对,我们就成了板上定钉的历史反革命家属。
儿时的记忆
1949年1月还没过年,北京被所谓的“和平解放”,在前门那儿搞了个进城仪式,共产党军队进来,国民党兵开出城。我那时还小,看着热热闹闹,挺乱的。
我母亲是老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的教育学。跟她要好的北大同学都是名人,比如画家张善子的女儿、齐白石的女儿。我妈爱唱戏,她可不是一般的票友,平时跟她走动的都是京城的名媛。
我们家住在东单一带,就是现在的北京火车站附近。那个胡同里住的都是国民党将军的家属之类的。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家的私宅有一亩多地,中间是个三层小楼,有十七间房子,和宋庆龄的故居差不多。中间有个月亮门,把园子隔成了前后院。前院住着卫兵,一个车库,有个草坪,上面种着一颗大香椿树,一棵梨树,一颗海棠树……1958年建北京站时,把我们拆迁到西边去了。
我小学上的是美国人办的私立基督教会学校。上教会学校的多是民国时期“遗老遗少”的孩子,像资本家呀,国民党的后代等等。
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个共军干部,带着一个小孩,后来我们管他叫田蛮子。他们听说教会学校办得好,非得把孩子送这来。他们可能看不上延安或解放区那个教育,觉得太土吧。
田蛮子是个混小子,挺霸道,瞅谁不顺眼就跟谁打一架,动不动就说:“要不是我爸爸(管着我)我就宰了你们!”别人都不敢惹他。他上了一个学期,就被他爸妈接走了,可能去上共产党专门的贵族学校——十一学校、八一中学去了吧。这革命接班人的苗子,不能搁在资产阶级少爷小姐堆里,这帮人是被改造的对象。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未来的统治者,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印象。
1949年刚开学的时候,教会学校学的还是民国的教材,《三字经》《千字文》啊,我至今还能背诵里面的句子:“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记得有一次,天下着雨,我的三舅当时还是个中学生,我让他给我画个小狗,画个小人,他就在我家房子的外墙上画小狗、小人。正好碰上防敌特的巡逻队穿着雨衣过来了,说 “哎!”把我三舅训了一顿,凶巴巴的,把我吓得够呛。我三舅带着我赶紧跑回家去了。
还有一次,我和我弟弟跟齐阿姨的孩子逗着玩,他比我大一点,我说他“跟小狗似的”。结果被一个警察听见了,把我和弟弟、我妈叫到派出所,问我是不是骂共产党呢?
所以,我们这种家庭孩子的命运,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幸亏我妈跟冯玉祥家的人,冯玉祥的父亲、他大女儿、他嫂子、原来他手下的兵,关系非常非常好。他的小女儿,我们叫她月亮姐姐,瘦瘦高高的。冯玉祥遇难后,她和她未婚夫回国,还到我家院子里来看看,说说话。我们家住15号,她家住12号。
还有,我姥爷是清末民初庚子赔款时期,和詹天佑一块送出去的学童,詹天佑被派去美国,我姥爷和他弟弟去了德国。学成回国后,正好赶上洋务运动,我姥爷当上了北京电灯公司的第一任总工程师。
在中共政权建立初期,这些关系对我家多了一层保护。
镇反运动:活得战战兢兢的
1950年下半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镇反”针对的主要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中共认为对它政权有威胁的人,包括已经投降了共产党,甚至于后来帮中共对国民党作战立了功的,都毫不留情,七里咔嚓杀掉。师长以下的都悬,军级以上的很少数人,出于统战的需要,才得以幸免。最初中共说过很多民主政治协商的漂亮话,全都不算数了,瞬间翻脸。当时在东单等大的胡同口,三天两头贴出各种抓人的布告。
作为我们这些国民党的遗留人员,整天战战兢兢的。我有个五姨夫,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他其实已经投降共军了,跟我五姨跑到北京来,住在我家。我妈叫他们这个时期不要出去,他们没听,出去了,结果就在东单那边,当街被抓住。
中共把他归为国民党里有血债的,打过仗嘛,抓住后就地枪毙了。我五姨也被抓走了,她可能在国民党军统里有职位,被关在北京南外城的“自新路”监狱,我妈带我们去探视过她。后来转到长春关押,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还关在那儿,关了30来年。
不光是军界,国民党北京市市长部的书记,她女儿我认识,叫林平,她爸爸的书法在北京是出了名的。有一天来人给他家捎信,说单位里有点事,今天就不回家了。其实他家人心里明白,那就是回不来了,枪毙了。时隔半年多毫无音信,半年后告个死讯完事。
东单那儿经常开公审大会,让群众去观看。当场宣判完,开着车押赴刑场,实施枪决。
镇反不到一年,全国大概杀了一二百万。那时人们就明白了:共产党要的不是民主,不是三民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的仁爱、礼义廉耻那一套,它要跟着苏联的阵营走,走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是强制的无产阶级专政,等于把治国纲领公开了。
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杀鸡给猴看呗。(就像《九评共产党》里说的,它是要让人们对它的威慑产生一种恐惧,在它面前颤栗,从此以后它就好统治了。它是有意这样做的。)所以从那时起,我们这些反动派家属就成天提心吊胆,说不定哪天刀就落到自己头上。
1950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封了关,原来边境没有护照也可以来回走,到那时就全部关闭了。
三反五反:我们老是敌人那边的
1952年,又开始三反五反运动。斗恶霸地主,收集“民愤极大”的,像南霸天、天桥五虎啊,按照正常量刑,绝对不够死刑,那时一枪就崩了。
什么叫恶霸?谁定的恶霸?比如有人控诉、检举你,说你欺负了谁,凑够了多少人,都这么说,就够恶霸了,就这么简单。比如咱几个捏鼓好了想害他,咱一说,不就成了吗?也不用什么法理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出很多冤案。
这时候我们就有感觉了:人家革命干部、贫下中农,都是正宗的“自己人”,我们老是敌人那边的,只要一来运动,就跟着紧张。
胡同口的小庙全拆了
“五反”里有一条反封建迷信(中共迫害、消灭宗教信仰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抓“一贯道”开刀,借这机会,把佛教、基督教、道教这些正教也打下去了。同时打击教会学校,将所有外籍神职人员、传教士驱逐出境。
我记得之前,北京几乎每个胡同口都有一个茶馆。有茶馆,附近就一定有个小庙,里面保留着小佛龛,老百姓管它叫土地庙。一片社区,比较开阔的地方就有一个大点的庙。一般供的就是观音菩萨、如来佛。也不一定都是佛道教或基督教的,也有的是为某一位历史人物,比如文天祥,建一个祠,它就成为当地民间集中敬香火的地方。
汉地是以佛教为主,那时在北京和天津,走到哪都是浓浓的佛教生活的味道,比现在泰国、柬埔寨的佛教气氛还要浓,逢十五、有庙会的时候,人们就去敬香。
信佛的人分两种:一个属于普通劳苦大众,整天干活挣钱吃饭,忙忙碌碌,可他也需要到那去买香、敬佛,这种信众最多。另外一些人生活好一点,比较郑重其事,一般都买香袋什么的。他们中有女士,老太太,也有年轻的,形成了一个社交圈。真正说起来,这是一个中国市民文化与宗教相互交织的社会氛围。
为了避免教与教之间发生冲突,有天主堂的胡同,绝对不会再建别的寺庙。北京白塔寺、广济寺一带有三个庙,都是佛教的,这附近绝对没有天主教堂,离它最近的天主教堂在隔了好几站的沙滩,道教在更远的白云观那边。这是从清朝那时沿袭下来的约定俗成的规矩,国民党时期也没人去触动它。中国古代信神的时间非常长,共产党以前的政府都不反对民间敬天敬神的祭祀活动。(政府的管理与民间的信仰是两回事,互不干涉。)
政府不但不管,还保护呢。如果有人骚扰宗教活动,警察可得管。他认为,你连吃斋念佛的人都打扰,你一定不是良民,是坏人。
日本侵华时都不触碰这个东西,他们要遇到宗教场所,也会合十,鞠躬施礼。
可是共产党一进城,烧香拜佛、进教堂、诵经都成了封建迷信。街道隔三岔五的开会,反对你做这些事。我们有个街坊平先生,是个教书匠,基督教徒,他们学校就专门组织这类人学习什么“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用无神论给人洗脑。
打那以后,我上小学的路上,再经过什么小庙的时候,突然就见不到有老太太背着香包进去的情景了,没人敢去了。你去了,很可能派出所或街道干部就找上门来,组织你去派出所学习。
老百姓这么多年的信仰,根深蒂固,拜佛的还有,变成偷偷摸摸的拜,别被街道发现。佛龛也给拿走了。1954年借着“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大潮,一下子把所有街道的小庙全拆了。
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牌楼也都拆了,街上的招贴画都是莫斯科之类的,当年流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共产党这套宣传鼓动特厉害,它造成一种“新社会来了”的假象,把你的信念、希望全转移到它那儿去,认为它这个比旧的那个要好,要高。国民党就不会专门给你宣传美国如何好,他没有主动给全社会洗脑的这种意识。
过去中国人教育小孩子,都拿敬天信神来教育,所以人们普遍心地都比较善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究要符合儒家的仁爱。自从宗教信仰被共产党灭掉之后,人的精神就没有了依托。
公私合营:只分过两次红,后来就没你事了
1956年我刚上初中,中国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改变所有制。农村要由原来自然形成的自由经济,变成合作社,城市要进行全社会的公私合营。我们那个教会小学也被公私合营了,与其它小学合并,名字也改了。
一上中学,政治活动就多起来,公私合营得跟着放鞭炮,跟着开各种集会,观看控诉资本家。
民族资本家的企业全部国有化,叫作国家收买,国家只给你一部分股份,然后才允许你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员。国有化是为了构成下一步计划经济的基础。
那些老字号,一得阁、全聚德、同仁堂的老板,都得上政协、北京市委去表决心。我家旁边有两个比较大的资本家,一个是双和盛啤酒厂的老板,东北人,哈尔滨的,第一个啤酒厂就是他们家的。他很聪明,干脆说我不要了,把啤酒厂全部捐献给国家。还有一个立升体育用品商店的王老板,原来在天津,立升也变成国家的了。我后来跟他儿子挺熟,据说那个股份,只分过两次红,后来就没你事了,也不敢言语。
原来老城区每个胡同的茶馆,里面摆一两桌茶座,有说相声的,说书的,唱大鼓的。供各个地方的人在这歇脚,住胡同里的人也经常在那下棋,喝碗茶什么的,就像这个社会的缩影,就像老舍的《茶馆》里写的那样。下棋喝茶得给钱,但非常便宜。人家唱戏,你愿意给钱就给,不给他也没辄,就跟张恨水写的《啼笑姻缘》里一样。
公私合营后,茶馆一下子砍掉大约三分之二,不让存在了。为什么?共产党就怕人聚在一起,它叫你莫谈国事。到1957年反右的时候,茶馆基本就没有了。原来那是私人开的,现在政府出点钱,强令没收,把窗户换成大玻璃,成了基层政府——居委会的办公地点,人家跟派出所有关系,谁敢惹呀?
反右中的荒唐事
那年的春天,寒假特别长,一共放了50天,我们都挺高兴。突然间开学了,发现我们那个语文老师怎么在那儿扫地呢?一琢磨,他肯定被划成右派了。其实他在语文教学上挺有本事的。
新一轮政治运动——反右派,疾风暴雨式地来了。前边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知识分子积极为国家出谋划策,添砖加瓦。其实共产党就想听好听的,让大家夸夸它,没想到说着说着,提出那么多意见,还很尖锐,最后这脸就挂不住了。后边又来了一轮向党交心,毛泽东把这叫“阳谋”,“引蛇出动”。
人们没有防备,包括那些非常著名的大学者、专家权威、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在鸣放中的言论,正好成为大批判的靶子,扣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全上来了,完全不讲理,出现了很多荒唐事。
我们班有个同学,他爸爸还是赴朝的所谓“志愿军”,他妈有个兄弟也在台湾。他向党交心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那个舅舅回来了。”然后他自己检讨,挖思想根源。紧跟着就被定为右派,说你整天想着国民党哪一天回来,要反攻大陆,你这人反动透顶。他就这样给自己找了个证据,挖了个坑,跳进去了。
各单位报右派分子的名单,要求有一定比例。人民群众当时就是比较傻,有的人说:“嗨,不是说凑数么,别拿这当回事”,以为就是个思想问题,教育一下就完事了。甚至有的基层小组长说:“人数还不够啊,不成我算一个吧。”这是真事,好多人都这样。他有一种所谓的共产主义心态,好像是别让别人受苦吧,这事还先人后己呢。
结果到了1957年下半年,只要定了右派的,该抓的抓,该处理的处理,有流放的,有进监狱的,有在单位里被监管的,去看大门、扫地。到1958年以后右派就变成阶级异己,敌我矛盾了,“地富反坏右”黑五类里有你一号,这帽子一辈子都摘不掉,你的孩子也被打入另册。
无意中的一句话记入档案
反右以后,学校和街道开始查每个人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登记造册,记入档案,把人分成不同的阶级阵营,对立的集团。1957年以前,成分不好的子女照样能上大学;1957年以后,就要以你所处的阶级地位为依据来分析你的思想状态、决定你的命运了,一个人从生到死,一切都跟阶级成分挂上了钩。
我们学校也发了表格,我活这么大,第一次自己填报家庭出身。
1958年我面临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我乒乓球打得好,在北京市少年宫、西城区队都打过,还参加过国家集训队的选拔赛,高校队的前五名里老有我,北京高校队老给我留个名额,让我作为特长生跟他们到处打球。当时八一队刚成立,在现在的国防大学里,它也招生,教练说我的基础没问题,能给他们拿分,应该去。可我想的是,以后怎么挣钱养活自己,就报考了中专。第一志愿是航空工业学校,因为我特别喜欢航空,从小学到中学都参加航模表演,还在中山公园草坪上拍过纪录片。第二志愿是北京某理工类学校。
报考中专我得了年级第一,离满分就差3、4分,但是航空工业学校没录取我,它属于国防工业,我因为出身的缘故,被扒拉下去。在第二志愿里我排行最高,被录取了。虽然我的专业高出别人一大截,但那时政治已经对位班干部,所以只当了一个学期的军体委员,就不让我当了。
对我打击最大的,是第一学期我的政治课成绩居然不及格,可是五分制的卷面我明明得了四分呀。我跑去找主管政治教研室的老师,他说:“其实你自己心里明白呀。”不管我考的如何,就按政治取向打分,非常严酷。从此,我的政治分每次都勉强及格,它跟配菜似的,你的政治表现加你的出身占多少分,从最高分给你扣除。所以我的基础分天生就低。
我妈了解我从小会的东西多,钻得深,一直告诫我:“人家能先干的事你不能去做。”她想的深啊:你活在这世上不容易,你会碰到很多事,我保护不了你,所以你要留意,不能像别人那样活着。我当时的想法很幼稚:把自己道德提高上来,莫谈国事,夹着尾巴做人,就可以保护自己。
比如兵乓球比赛,是不是需要你去给班里争荣誉?我不去不行,去了尽情表现,也坏了,他认为你是别有用心。我去了也要拍马屁啊,如果把他们都打败了,我就完蛋了。开大会时,别看大家都喊“毛主席万岁”,你喊的味儿可就不一样了,最起码我得小声点,悠着点,我要使劲喊,人家会说我是故意想怎么着。同样一种表现,阶级本质不同。那时我才17岁,可是平常我比别人考虑的多得多。
开会的时候,上面的人讲话,我在底下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虽然没说我,但是扎耳朵,就跟说我似的。
那时同学们都对我侧目而视,没笑脸。我们去工厂实习,工人里有特别激进的,党员什么的,开小组会时就说:“你呢,家庭出身不好,在我们这要加强学习改造。”带我那个师傅私下问我:“哎,你是国民党中将的孩子,你见过你爸么?”他告诉我,来的这批孩子,有五个是需要改造的,他们工人提前开小组会打招呼了。所以后来我干脆自己直接跟工人说:我需要加强改造。
我们班团支部书记是个女孩,比我大一岁,她开始挺喜欢我。有一次晚自习,她和班主任跟我一起上楼梯,和我聊天说:“最近政治学习,你对蒋介石和杜勒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有什么看法吗?”我说:“杜勒斯有杜勒斯的观点,有他对整个世界的各种看法、做法吧,这是美国;蒋介石有蒋介石的看法,毛泽东还有毛泽东的看法。”
没想到这么一句话,给我记入了档案,记成这样:毛泽东有毛泽东的观点,蒋介石有蒋介石的观点,你有你的观点,那你的观点偏向哪一边呢?啪,画了一个问号,里面潜台词就多了去了。一个班主任,一个团支书,就有权力给你塞档案,但她不告诉你,我连个防备都没有,你问我对国际时事的看法,这话也确实是我说的(有口难辩)。后来班里老开班会,说,大家的思想参差不齐,但你不能反动,你应该跟国家、跟政府、跟党走。这话就是敲打我呢,我知道。
事后,那个团支部书记悄悄告诉我,给你塞档案了,是老师出的主意,“哎,你怎么那么傻呢?”那老师大学毕业刚两三年,她已经有这意识了。这些底层的党团干部,平时都带有党交办的政治任务,脑子里总转着:设计一个什么政治场景,制造一个偶像或对立面,编出点故事来,就分出敌友来了。其实她无非是想自我表现,给自己捞资本。
这事让我特别气愤!但我表面不能反映出来,我不吱声。
差点成为反动学生
1958年大跃进,我们学校停课,跟着全国大炼钢铁。三年大饥荒来了,又跟着全国一起挨饿。那时党也蔫了。直到1963~1964年,经济一有好转,共产党马上又折腾,狠抓阶级斗争,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一波接一波,进一步强行撕裂这个社会。
我们学校整班并入一所高校,那时我已是大三学生。学生里也要求以阶级划分三六九等,我在我们班无争议划到最低一等,我爸还在台湾呢,我就是敌特家属、反革命家属,属于敌对阵营的。在学校我基本不说话,如果非让我说话,我就骂一骂蒋介石完事。
你说我自己找个角落呆着去吧,不行,开会你还得去,你还不能不发言,你要不发言,不整天给共产党唱赞歌都不行;另一方面,你要不批判别人,不参与整人,你又有问题。
早期还有一些同学对我有怜悯心,后期就绝对要跟你划清阶级界限了。如果两个人一块走,会尽量避开你,最好是有别人在场,免得说不清楚。那时同学之间已经不敢交心了,互相防着,即使俩人关系好也那样。
到1964年下半年,小绳越勒越紧,掀起抓反动学生。这时我再谨慎都不行了,同学里有人专门贼着我,想听我是不是说反动话。
那天白天我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说一个孩子打篮球打得不错。这时一个姓高的同学就出去了,过一会,班长来了,看了我两眼。别的同学告诉我,高某找班长打你小报告:你瞧李北海又自个儿在那叨咕反动话呢。他想表现自己阶级觉悟高:人家都没听出来我听出来了。
班长把这事汇报了,系里找我谈话。其实我当时说的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人家正在甄别反动学生,我差点就成了典型。
这次弄出一大批反动学生,比右派学生要多,都是些20出头的孩子。
那时候才十几岁,心里很难受吧?真正到那个程度,已经不是心理的事了,生理上就好像被搁在真空里,特别憋得慌。那还能思想吗?你要想活下去,你就别思想。有那么几个学生独立思想了,有所表露,被扣上“该生长期思想反动”,开除学籍,送去劳教。
毕业前,系里和班干部反复找我谈话,说你现在能在这儿学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本来你是没有资格完成学业的。可能因为我的专业成绩太好了,我的毕业设计图后来在中国科协的展室作为标准图长期展出。我还做了一个小设计,是汽车上用的计程仪,当时国内的机电一体化技术还达不到,我把它寄到机械部,被认定是一个很好的设计。我把其中最先进的部分通过朋友送到德国。
可是,我在政治上的一举一动,包括敌特家属的身份,全都被详细记录,积累了厚厚一摞档案材料。那些年我就觉着,我一直在严密监控下活着,一次次的紧箍咒,用得着你时还得用你,可是又拿你当异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翻脸。我只求别老这么折腾我行不行?你说我一个小孩,在这人世间是什么感受?那种恐惧无处不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非常难熬,就盼着赶紧毕业。
一个等待判你死刑的地方
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交通局,正在陪局长出差的途中,“文革”起来了。北京市各个系统下面的厂矿企业纷纷成立造反派夺了权,他们有一个联合集中的总司令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叫“北京红色造反者”。
我这种出身不好的人,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是被专政、碾压、扫除的对象。不久,我就被造反派关入了集中营。那是1966年。
那天在单位开完会,我被押上一辆卡车,直接拉到北京北部的西三旗,北京工矿企业的黑五类集中关在那里。周围用铁丝网圈起来,中间几个帆布帐篷。往东去,是一个劳改砖厂,再往东,就是北京市劳改局了。我们这个点关了大约600多人。红卫兵、造反派在北京大概建了五、六个这样的点,规模都差不多。高中生里的黑五类也有他们的集中营。
在那每天做什么?等死啊!那儿就是一个等待判你死刑的地方。
哪个地方要搞阶级斗争了,就把我们拽出去,像拉出头猪,拉出条狗似的,拉到那儿去挨批斗。斗争完了,死了就死了,没死就拉回来搁着,明天再拉到别的地方。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前,中山公园音乐堂的露天剧场,大学校园,都是开批斗大会的现场。
每天谁去挨批斗,由看守我们的造反派决定,他什么根据都没有,看谁不顺眼,想弄谁就弄谁。比如北京航空学院来了一辆车,需要斗几个人。他就看看,“这个!那几个!那谁谁谁,你,去去去!”凑一车人,每个人挂上大牌子,上边写着你的名字,“走!”
天天都有打死人的,有人出去就回不来了,回不来就知道已经死了。那个心,随时都悬着,真是命悬一线的感觉。
天天都得出去挨斗,天天挨打。捅你两棍、踢你两脚那是好事。即使侥幸回来了,那个工人造反派很粗鲁的,他今天突然来气了,想发泄一下,“出来,站着去!”拉出几个站成一排,你不出去踹你两脚。他觉着过了瘾了,显示完他掌握你的生杀大权了,拿着棍子,咣!“滚!快回去!”
陪斗王光美,亲眼看到打死人
高校系统要斗争王光美,找高校系统的人去陪斗。一查,这还有一李北海哪!之前那些档案记录全起作用了:这样的反动学生怎么能让他上大学?还能让他毕了业!
批斗大会在北工大的大操场举行,开了两个多小时,一共17个人挨斗。搭的这盘菜里除了走资派代表王光美,还有执行那条反动路线的干部,如全国高校部的副部长宋硕被揪去了。还有走资派下属教育系统里的教师、反动学生。拽我去,是想证明我是这条线上培养出来的资本主义苗子,坏典型。
那次大会非常著名,级别非常高,是全国性的,受到最高层中央文革小组的主使。电视台都去了,录了像。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都来了,会场边上插满了旗子,什么北航红旗,地质学院、清华、北大、北工大、工人阶级的支持队伍等等。蒯大富、谭力夫等红卫兵领袖也去了。
罗老师,是北工大化学分析专业的教师,被当场打死!死的时候才40岁。他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就成了教育系统暗藏的反革命,说他经常有反动言论。
打他的时候,不让我抬头,但我在那边可以看到。他们把他一脚踢到台下去,叮了咣啷,上来一帮人一顿暴打。打完之后,还说他装死,把他提起来,那时他还能站起来。接着又打了一顿,他就站不起来了,跪在那儿……慢慢就把他拖走了。后来就听说人没了。
非常巧,多年后我跟他儿子又认识了,一聊才知道,哦,这是当年被打死的罗老师的儿子啊!他告诉我,斗争他爸爸的时候,他妈只有30岁,被关在屋子里,红卫兵把守着。他那时很小,只有五六岁,他表弟也跟他们住在一起。当时家里亲戚没敢告诉他们实情,过了一段才知道,人已经被打死了。
我挺皮实,也许命不该死。后来我的母校开批斗会,又把我拽去了。那次又打死一个人,是位教语文的女老师。她离我不远,我听她只说了一句:“我不就是个教师吗?”那帮人不是一下子给你致伤,是长时间慢慢折磨死的。拿着皮带上来一拨人打,一般打个三五分钟,打累了,又换另一拨上来接着来,一打打三四个小时。打到最后,不省人事了,他还不认为人会死,还认为是装死呢,再踢上两脚。最后看实在不行了,躺半天了,就拉走了。
这些人打死一个人没有一点愧疚或惧怕吗?他们认为这都是革命行动,表示自己对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觉得这个人该死!就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阶级感情,阶级仇恨吧。另外,他觉得自己根本没责任,不是我打死的,他觉得跟自己没关系。
目睹、经历这些事,当时是什么心情啊?待会儿没准就轮到我啦!大难临头的感觉。一咬牙,等着呗,没有太害怕。回去倒有点感觉:今儿怎么又活下来了?没有恐惧,就是难受:哎呦,今天又走了几个。想想觉着,活着又有什么劲呢?
每天他们回来了,你们也回来了,几拨人回来了,大伙彼此都没话说,没什么可说的。跟他说心里话没有任何意义,没准明儿他就死了,也没准是我,就那种状态。
从1966年夏天8.18以后,到1967年上半年,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完完全全的红色恐怖!(当时红卫兵的口号就这么提的:红色恐怖万岁!)
正好是从秋天过了一冬,那个帆布帐篷的地面弄了点草,弄了点席,没有火,更没有暖气,就睡在地上,这么冻着。那多冷啊。那活该,谁管你冷不冷?那时候人死了很难区分是冻死的还是打死的,也没说病了还要就医,对你们来说没有这个,就没把你们当人。
(未完待续)
口述:李北海(化名)整理:天诚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4/22/n14489164.htm)